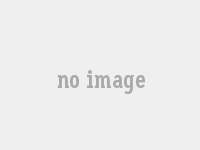“负利率”是当前全球金融格局的一大显著特征。
为了遏制通缩,推动本币贬值,欧洲、丹麦、瑞士、瑞典和日本央行分别于2014 年6月、2014年9月、2014年12月、2015年2月及2016年1月开始把其货币政策利率降至负利率水平。进入2016年,实施负利率政策的国家和地区在扩大,负利率程度在增加,其覆盖范围从商业银行在央行的存款进一步扩展到银行间市场和国债市场,而且更多的国家还在酝酿减息、或者执行负利率政策的可能性。目前,中央银行采取负利率的国家GDP占全球GDP的23.1%,其中欧洲央行和日本央行覆盖地区的GDP占比达21%。而从实际负利率政策角度看,那些通货膨胀率大于名义利率水平的国家(地区),也会出现负的实际收益率。
目前,全球负收益率国债规模达到13万亿美元,比去年的5.5万亿翻了两倍还多,而2014年年中几乎还没有负收益率债券。发达经济体和新兴经济体债券规模和增长速度都很快。目前在全球的存量主权债券中,名义利率为负的比重达30%,名义利率介于0%-1%的低利率区间的比重为35%。不少长期、超长期的国债收益率也进入负利率时代,最长的期限如瑞士30年期国债、日本15年期国债、德国10年期国债。但是,发达国家这种货币超发及“负利率”政策并没有带来新的经济增长,反而使全球经济潜在增长率趋于下降,为新的系统性危机埋下了金融隐患。
对实行负利率的中央银行而言,一再压低关键利率至负值确实拆开了困局下的最后一道屏障。然而,低利率及负利率政策给长期经济稳定增长带来了极大的负面效应。在长期债券购买和低利率政策刺激下,全球劳动生产率却增长缓慢,表现为金融对实体的“挤出效应”,市场表现为信贷过度宽松,使得资源转移到更为低效的部门中,生产率的降低在危机后将会持续。据测算,2008至2013年,经历金融繁荣和萧条周期的发达经济体年均损失了0.5个百分点的生产率,而这一损耗很可能是难以短期恢复的。
在表现形式上,负利率政策突破了传统货币政策的零下线限制,给予了货币政策更大的发挥空间。在政策目标上,负利率一方面增加了持有存款的成本,降低了融资成本,从而能促使金融机构将过剩资金投放市场,鼓励投资、信贷和消费;另一方面压低了汇率,利于增加出口。然而,这种政策实践的负面冲击已开始进一步显露。受两大周期的矛盾影响,国际金融市场出现了非美国银行借入美元资金成本高于其借入本币资金然后换取美元成本的现象。特别今年年初以来全球金融市场动荡的催化剂使负利率下银行的净息差减少,盈利能力持续下降,欧洲银行业股价重挫。包括德意志、法兴、瑞信以及意大利等主要欧洲国家多个金融机构信用违约掉期CDS大幅上涨,信用风险攀升。
在负利率时代,安全资产供不应求,这就是所谓的“资产荒”。国际油价反弹,黄金等避险资产备受欢迎。今年以来,投资者对大宗商品的投资已逾500亿美元,为七年以来每年2月至7月最高水平。上半年,大宗商品市场表现优于债市与股市。
本质而言,全球这场负利率货币实验看起来是非常规的宽松政策,然而,实际上银行的信贷紧缩风险却未得到根本解除,对全球金融市场的长期结构性影响绝不能忽视。
从弗里德曼法则角度看,负利率政策绝非最优。因为在名义利率为负的情况下,相比以定期存款等财富形式,持有货币会带来额外收益,个体会过多地持有货币。虽然负利率政策在理论上可以在一定程度上促进银行放贷,降低融资成本,促进消费与投资,但事实上,银行的信贷是否扩张取决于银行放贷意愿、市场的需求、市场的信心、资产负债表的健康状况,负利率也根本解决不了“流动性陷阱”问题。
长期供给廉价资金将大大增加资产泡沫和投机的风险,进一步推升债务压力。比如,欧洲央行的LTRO带来了低成本资金,银行可购买政府债券通过套利交易获利。一方面,资金淤积在金融体系,银行剩余资金可转向投资资产回报率较高的高风险领域,或从事较高风险资本操作来实现短期资本利得;另一方面,由于政府债券成了银行可抵押品的重要部分,成了金融机构趋之若鹜的投资品,这又促使政府债券供给增加,从而推升了整体债务总规模。
负利率政策是在全球经济增长停滞及通缩的双重压力下产生的,其背后的结构性问题是长期资本和投资回报率下降,因此,如果负利率政策持续下去还将通过实体投资回报率的下滑降低长期实际利率水平,并导致名义利率进一步下降,由此形成相互影响、相互加强的“负向循环”。
负利率政策还将通过汇率和国际资本流动渠道释放出来,“放水竞赛”已成囚徒困境。在逆全球化趋势及负利率政策预期影响下,各国竞争性货币政策会卷土重来,全球资产价格的波动会因此变得更加动荡。
因此,如果当前全球危机救助形式不发生根本性改变,不排除未来再次发生全球系统性金融危机的可能性。
(作者系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副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