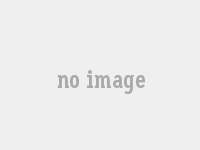编者按:这是一篇近年来不可多得的重要学术批评文章,一经在《中国文化报》发表,便引起了文艺界关于问题与标准的热议和讨论。作者以犀利的文笔对当下“轻视问题、空谈标准”等的不良学术风气进行了有力地揭露和批判。著名理论家张弛对此文评价说:“胡适1919年在《每周评论》发表了《多研究些问题,少谈着“主义”》一文,挑起了问题与主义的论战。王进玉2020年在《中国文化报》发表了《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标准”》一文,引发了文艺有无标准的讨论。两篇都是作者各自在人生最意气风发的年纪,以学者固有的文化自觉和高度的社会责任感写就出来的针砭时弊、切实所需的重磅文章,不仅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还将具有深远的历史影响。”全文如下:
不得不说,无论文艺创作,还是文艺批评,动辄就大谈所谓的“标准”“权威”,都是极不正常的事情,也是学术界、理论界的通病,最需警惕的地方。真正的文艺家都清楚,文艺创作不是科学研究,更不是流水生产或工艺复制,它不需要那么多清规戒律、条条框框、公式套路等的限定和束缚,它是无标准更无权威的,甚至说它天生就带有反标准、反权威的属性。
如果一个文艺家,张口闭口就大谈标准,或是用所谓的权威来压倒对方、指手画脚、狐假虎威,那么他一定是伪文艺家,也一定是不折不扣的教条主义者、权势主义者。倘若文艺非要有什么标准的话,也应该是多元且丰富的,否则就失去其创作本身的趣味、价值和意义。而解放和繁荣文艺的最好方式,从根本上说也是要去标准化、去权威化,再加上一个去行政化,从而做到自由竞技、百花齐放、百家争鸣。
众所周知,古今中外任何名垂青史的文艺家、文艺流派,都不是标准化出来的结果,都带有鲜明的自我风格、特色,甚至带有离经叛道的特征,无论在中国美术发展历程中,水墨为上的理念对“随类赋彩”“以色貌色”等“重色”色彩观的分庭抗礼,写意绘画对工笔绘画的平分秋色,八五美术新潮对传统文艺的集体反思,以及对新创作观念、技法等的自觉寻求和探索,还是西方艺术流派里,巴洛克艺术对文艺复兴时期主流艺术风格的打破,新古典主义对巴洛克艺术、洛可可艺术的厌恶,浪漫主义对学院派和古典主义的摆脱,现实主义对浪漫主义的转向,印象派对学院派的抗争,后印象派对印象派的不满,那比派对印象主义的回击,象征主义对理想主义的逆反,立体主义对固有画面的重构,抽象艺术对具象艺术的超越,达达主义对传统文化和美学形式的废除,野兽派对后印象主义的改变,包豪斯学派对复古主义的批判,新造型主义对创作个性的消解,波普艺术对约定俗成的评价标准的破坏,至上主义对传统艺术的否定,极简主义对抽象表现主义的革命,后现代主义对现代主义艺术的拒绝,概念艺术对实物表现的取代,新表现主义对波普艺术和极少主义的反动,反概念主义对概念主义的检省,等等,都基本说明了这一点:文艺创作尤其艺术创作,没有一成不变的标准,也一定不是墨守成规、因循守旧的,其都在否定与自我否定中逐渐建立起来并自成体系,否则只会被模式化、同质化、套路化、概念化,只会循规蹈矩、陈陈相因,诞生出一批又一批的流水工、复制品,从而严重阻碍着文艺真正的发展和进步。
此外,翻阅历史以及从上面举出的例子都不难看出,国内并没有出现像国外那样如此多的艺术单元和流派,如此纷呈的艺术理念,如此活跃的创作氛围,其发展进程与形式表现也没有那么明显和丰富,且具有各自相对完整的体系与脉络。这其实也正是核心问题所在,反映出从古至今我国艺术发展相对缓慢、滞后的一个重要原因——不管是我们的艺术思维还是实际创作都太规矩太老实了,总是在前人既定的所谓的标准框框里打转,在国画还是油画、水墨还是色彩、工笔还是写意等寥寥可数的几个传统门类、内容形式上翻来覆去的讨论、反反复复的实践,而对其他文艺理念,以及诸如非架上艺术的装置、行为、影像、新媒体等其他艺术样式知之甚少,更缺乏必要的发散思维和探索创新的勇气,甚至迄今为止仍有相当多的人不把它们当成艺术看待,这是很可悲很无奈的事情。
毫不客气地讲,此现象与问题的形成,很大程度上就是“标准”惹的祸。现实中我们总是在不断地、强行地制定和灌输一些似是而非的标准,并有意无意间告诉他们应该这样不应该那样,这样做是好的那样做是不好的,以致于让大家误认为“标准”之外的,都是不对的,都是错误的、不入流的,都是不受欢迎、不能接受的,由此也便极大扭曲和误导了大家对文艺本该正确的理解和判断,桎梏了对文艺无限可能的想象与创造,这是很不应该的,也是须立即停止的隐性文艺毒害行为。
所以在这里要特别强调,无论艺术家还是理论家、批评家,套用胡适的话说就是,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标准”。其实标准很容易谈,也好制定,动动嘴一二三四条,乃至更多条就有了,但关键是有没有那个必要,违不违背艺术属性,贴不贴近创作规律,符不符合发展实际,产不产生负面影响,这些都是要重点考虑的,也是要负历史责任的,而非信口开河,盲目片面地下结论、树规范、定标准。
何况现实情境也往往是,所谓的标准有了,人也跟着变懒了,变胆小了,懒于分析,懒于创新,懒于求变,或创作上胆战心惊、如履薄冰,不敢越雷池一步,而做为评判者评判起来自然也会变得更加省事和方便,更加蛮横与独断专行,不管三七二十一,凡事都往标准上靠,拿标准来统一衡量、裁决,丝毫不在乎文艺的个性化、差异性问题,举凡不符合标准的就被判定为不合格,就被认定有瑕疵,甚至被视作异类予以排除、打压或雪藏。殊不知,这无疑是对文艺创作,尤其是对文艺创新的极大扼杀和戕害!
须明白,理论家也好,批评家也罢,都没有这个生杀大权,你的身份和职责都不允许你那样做,你所设定的那个标准可能只是你个人有限的、粗浅的认知,只是个伪标准,并非文艺创作本身所天然具有的法则与尺度,尤其在事物还没有完全发展成熟,在你并没有任何实践、体验的前提下,只靠一时的主观臆想、史料分析或逻辑推理而做出的判断,很多情况下会比文艺家实际的、鲜活的创作更容易犯错。
当然,这里并非否定理论研究、学术评价等的作用,只是在告诉那些自以为是的“权威专家”们,无论何时,还是要脚踏实地、求真务实,多关注多解决些文艺创作上出现的具体问题,少空谈些看似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和“标准”,实则大都是自欺欺人、自误误人的纸上谈兵罢了。(注:本文作者王进玉,知名艺术评论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