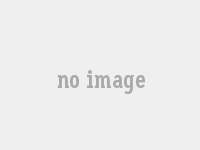近日,著名作家余华被某教育机构邀请,发表了一场演讲《如何写好中高考作文》。消息一出,朋友圈、微博、豆瓣上都出现了对此事热烈的讨论,更有网友感叹这意味着“文学已死”。
余华在演讲中。
为何余华的这场演讲会引发如此大的争议?这背后最直接的原因,大概是文学创作与应试写作有着巨大的差异。但在本文作者看来,余华“指导”中高考作文,成效如何根本不重要,线上教育机构邀请余华演讲,本身就是一场醉翁之意不在酒的秀。重要的是,通过这场演讲,甚至这场风波、争议本身,线上教育机构扩大了它自身的影响力。
也正是在这里,我们看到了资本、市场巨大的“收编”能力,但是我们也别忘了,文学的力量也是巨大的,对于奔涌的时代,它也有着巨大的消化与转化能力。从这个意义上来看,当这二者相遇,会产生怎样的“震动”或“火花”,仍然挑动着观众巨大的好奇心。
撰文|重木
为何作家讲作文会引发争议?
我们经常看到这样有趣的新闻:某作家发现自己的某篇文章被初高中语文试卷收作阅读理解,然而当他们自己答题时,往往很难获得高分。在这个时常引人一乐的小事背后,其实涉及了诸多令人无奈或是无法控制的事情,诸如文学本身的复杂和多义性使其内涵并不完全取决于作者本身,读者作为理解与感受的能动主体在其后的法国文学理论中变得更加重要;另外就涉及初高中语文本身的自成一体系统,导致在很大程度上它几乎与我们所认为的文学或是相关的文学创作没有深刻的联系。也正是这一现状以及其中隐藏的吊诡,让许多网友在看到余华参加一个线上教育活动教授高中作文写作时感到了诧异和不解。
如同许多评论文章所指出的,以余华当下中国著名作家的身份,指导初高中作文写作本身是无可厚非且绰绰有余的,但人们也会立刻发现,当余华成功的文学创作经验遭遇现实中的范式性极强的高中作文写作时,捉襟见肘或许是更加真实的情况。倒不是因为余华自己的高考失败使其失去教授高考作文的资格,而是在很大程度上作家所从事的文学创作与初高中生所要求写作的作文之间存在着很大的隔阂。
余华在教育机构的演讲活动上。
这一隔阂所涉及的其实是广义文学之下一个实用性写作,它本身与前者之间存在着鲜明的紧张关系。而也正是这一差异折射出当下的应试教育训练在很大程度上只能应对其有限领域,尤其是语文的基础学习与写作。
现代教育中出现的考试本身是作为检测学生所受教育情况以及由此作为公平公正的选拔手段来挑选人才。对于有着源远流长科举制度的中国而言,现代教育在学习西方模式之时也依旧在许多方面保持了相关的传统因素。而无论是余华所参加的这一线上教育活动,还是这些年在国内兴起的补习班等教育宣传、活动和课程,也都是这一大背景下的产物。教育作为个体成长中最重要的事情,也依旧如曾经一般裹挟着个体、家庭、社会阶层流动以及地位等方方面面因素。
余华在1977年恢复高考后并未如愿折桂,最终在父母的帮助下开始学医,其后在80年代的新文学风潮中进行文学创作,最终随其代表作《活着》的问世成为其后赫赫有名的先锋作家中的一员猛将。余华本身经历过高考的竞争,但从上世纪末恢复高考到当下,无论是接受教育的人数还是高考的竞争激烈程度已经非往日可比。正是在这一“千万人过独木桥”的状况下,高考一方面保留着其本身的目的,即作为选拔和检验人才的公平手段;但另一方面它也渐渐成为一项可以通过精打细算、精心准备而能够成功应对的测试。这些特点当然与文学创作极为不同。
线上教育机构为何请余华演讲?
在余华题为《如何在中高考中写好作文》的演讲中,作家并未长篇大论地言述文学写作或是文学理想,反而是一篇十分细致的实用写作指南。例如,如何写好作文的第一句、如何在论述文中利用诸如“几天后、几年后”这样的句子来收拢主题等。这些颇为实用的写作高考作文的技巧,我们可以在许多相关的教科书或是指南书中看到,余华所说的东西本身并不具备很大的创新性,属于高考作文辅导圈内的常识。对于经历过高考作文训练的学生而言,帮助或许十分有限。
但我们或许可以从另一个角度来思考:为什么此线上教育活动会请余华来做这篇实用性一般的演讲?是他们真的觉得余华能为这些高考的学子在作文写作上提供什么实质性的帮助吗?答案或许更加复杂。
这些年随着各类教育机构的兴起,邀请名人代言或授课的模式也普遍出现,如张泉灵的语文课便在网上大肆传播。利用名人与其说是看中他们的能力,不如说是看中他们的名声及其文化资本,尤其是像余华这样声名远播的作家。当教育培训得到具有丰厚文化资本的名人代言,其影响力和公信力也必然得到巩固,从而能够吸引更多家长的关注和消费。
余华代表作《活着》
就以余华所参加的这一教育活动来看,坐在下面听讲的与其说是初高中学生,更可能是他们的父母。因此,与其说作家这段不足五分钟照着稿子念的演讲是教初高中生写作文,不如说是给那些被卷入当下教育焦虑中的父母上一节心理安慰课。演讲者到底讲了什么或许不再重要,反而是演讲者的身份更能吸引他们。这也正是教育机构邀请名人代言或出席此类活动的重要原因。网友也大都直观地感受到了这一点,才会把余华出席此类利用其文学名声来牟利的活动,提升到“文学已死”的耸人听闻程度。
真正的问题不再是余华是否有资格或是能力教初高中学生写作文,而是对教育机构而言,重要的是“余华”这个文化品牌,至于他的演讲中的各种实用小技巧大概可以看作是可有可无的绿叶。也正是在这里,我们看到处于其中的余华本身的困境。作家介入作文写作,或许能对作文的套路与模式进行一些更新,但当他真的按照教育机构给出的题目参与到实用性写作指南的演讲中时,他其实便被裹挟进这一由资本、教育机构以及应试作文等所形成的场域中,成为其中推波助澜的一分子,并且由于其特殊的文学声望而导致网友们的批评和不满。
在这些批评中我们便会看到那个看似古老却实则始终存在的一个信念,一方面是对于文学创作的美好信仰——如文学本身因其“无用”而形成的无功利性;另一方面则涉及当下知识分子在面对社会中所存在的各种问题或焦虑时所扮演的角色。在许多批评中,人们都强调文学创作本身的自由和独立性的重要,而批评考试作文在竞争和内卷的压力下而日渐“八股化”的趋势。在一定程度上人们建构了二者的对立。试想如果余华参加的活动是教授大学的创意写作呢?或许便不会引起此类批评。
人们对余华出席此类活动的揶揄也反映了在这个被商业与消费大潮所席卷的社会中,传统曾经作为话语主体的知识分子在日渐退向边缘时,大众对其的期望和想象。当人们提起曾经作为极具颠覆性的先锋派作家都开始参与商业活动时,其中的感慨与无奈或许一言难尽。
文学与资本,都具有巨大的消化能力
这些年随着众多学者、作家、教授和其他知识分子开始参与大众传媒或娱乐活动时,人们对其的态度也模棱两可。但是当刘擎教授参与《奇葩说》,以其清晰透彻的理性观点批判那些存在于日常和生活中的种种问题时,依旧获得了网友的称赞。似乎无论社会如何变化,人们依旧希望知识分子能够以其清晰且极具批判性的立场和见解来拨开惯常中的层层迷雾与揭露出那些包着毒药的蜜糖。余华所参与的这个活动——就从流出的演讲视频来看——似乎并未与人们所想象与期待符合,因此诸多批评中的失望之情也始终若隐若现。
余华暌别八年的新作《文城》在年初出版便引起了颇大的关注,对其感兴趣的读者都在翘首以待。对于当下中国文学生态而言,能够引起相关圈层如此关注的作家新作或许屈指可数,这也再次从侧面折射出“余华”这个名字以及与他联系在一起的文学创作和可能性所具有的力量。
《文城》,余华著,新经典文化|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 2021年3月
对新作评价好坏暂且不论,我们在这里更想指出的其实是伴随着知识分子(包括诸如作家、诗人、学者与艺术家等)的“世俗化”以及他们在面对磅礴的消费主义、资本和多样的市场与大众娱乐时,曾经对其的要求或评价标准似乎却依旧未出现很大的改变。一方面,他们被置于已经消逝的“神坛”上但仍被要求承担起责任和义务;另一方面,当他们向下看的时候却发现前面早已经空空无也,当他们面对令人眼花缭乱的大众娱乐与消费社会时,往往发现自己原本的一套语言已经难以展开有成效的对话。在这一零落的现状中,实用、有利和如何成功成为主流,一不小心知识分子也便落入其中,成为其牌面。
问题的复杂之处也正在此,现代应试教育本身所牵连和涉及的因素因其庞杂一时间难以厘清,反而是随着应试人数的上升、工作职位的有限以及社会竞争压力的增加而导致其进一步地被推崇成为阶层流动的主要途径。内卷因而在教育领域中加强,出现当下普遍的教育焦虑。也正是在这一焦虑的土壤上使得各种教育机构趁机大展手脚,利用各种营销、广告与宣传来挑动、迎合父母们的焦虑。
对余华来说,由此引起的议论和批评却不仅仅是他是否有能力教授初高中生写作文,反而是人们对文学创作与应试作文的矛盾以及作为知识分子的职责等义务的怀疑。人们从余华这一行为上所遭遇的破灭之所以看似远远超出了这一件小事所能蕴含的意义,或许正是因为它再一次展现了现代资本和市场所具有的力量,以及知识分子在面对相关问题时可能出现的逡巡与无奈。
人们想象或是希望文学会是自由且独立的,因其无用而有趣和极具可能性。而“余华”在某种程度上作为一个与文学相关联的符号,依旧为许多人所念兹在兹。最终他也出现在这场汹涌的浪潮之中,让人们在诧异中感受到荒诞的现实。但在这些批评之外,文学与资本的互动会生发出怎样的震动或“火花”,仍然可以是一件令人好奇的事情。
作者 | 重木
编辑 | 走走;王青
校对 | 王心